胶原蛋白肽是什么提取的?为什么医生不建议喝胶原蛋白肽
胶原蛋白肽是什么提取的?为什么医生不建议喝胶原蛋白肽
胶原蛋白肽是什么提取的?为什么医生不建议喝胶原蛋白肽美甲如今是很多女孩子的(de)日常。说起来我(wǒ)也美甲了很多年,从记事儿起就算是开始(kāishǐ)了,直到现在五十多岁也还在进行中。只是我的美甲史有些特别:从没有进过美甲店,没花过一分钱。我的方式非常古早:用的全是指甲(zhǐjiǎ)草。
在我小时候的杨庄村,只要有女孩子的人家,必种有指甲(zhǐjiǎ)草。也有叫指甲花的,都行(dōuxíng)。花草不分家么(me)。我爱叫它指甲草,草的感觉更有力道。
指甲草极皮实极好养。春天撒下种,隔三岔五给它浇点儿水,其余就(jiù)不用再操心,不几天就出了(le)两芽儿嫩嫩的翠苗儿,出了苗儿,就一天一个样儿,像女孩子的身子一般,葱葱茏(cōnglóng)茏,苗苗条条地,就长起来(qǐlái)了。等到了初夏,叶子就抽得细细的、长长的,叶子根儿那里就打起了绿色的小苞,这时候(zhèshíhòu),就该开花了,一开就是一个长夏。
指甲草(cǎo)开起花时,白的(de)、粉的、黄的、紫的、大红的……对了(le),还有两样儿女孩子们叫它们花花儿(huāér)——花的花儿,有点儿绕口,开的是白底红晕和红底白晕的花,是最名副其实的花。这些花都是好看的。当然,更好看的,是这些个指甲花开到了女孩子们的指甲上。说来奇怪,无论(wúlùn)什么颜色的指甲花,染到了女孩子的指甲上,都一样是红的。
那时候,在这(zhè)乡村里,染指甲(zhǐjiǎ)似乎是女孩子们(men)的(de)必修课。课上了一代又一代,染法倒没什么大(dà)变。先把开饱的花儿摘了,在太阳下晒晒,去(qù)去水,然后放到碗里,加上点儿白矾,用蒜锤子捣碎了,一直碎成花泥,这就成了染料。至于包(bāo)指甲的叶子,都(dōu)说还是用指甲花的叶子最好,原叶配(yuányèpèi)原花,染出(rǎnchū)的指甲最是漂亮,可是用它来包的人却少之又少。因用它包需要两样铁板钉钉的功夫:一是包的功夫。它的叶子只比柳叶大一圈,用来包指甲显得过于窄小,容易让花泥跑出来,滴滴答答地蔓延一手。二是睡觉的功夫。即使好不容易用这叶子包好了指甲,睡觉时要是不老实,胡抓乱挠的,半夜里也很容易脱落,末了(mòliǎo)还是洋洋洒洒处处红。因此,若是这两样功夫都平常的女孩子,是绝不敢用这叶子包的。
通常用的(de)都是豆角叶。豆角叶是圆圆的桃子形,叶面阔大厚实,韧性好(hǎo),包起来最是趁手。包的时候,只(zhǐ)需将花泥(ní)在指甲上按瓷实,然后将两张豆角叶交错叠放(diéfàng)在指肚下面,自下而上,将指甲轻轻包裹起来,再将指尖外多出的那点儿豆叶(dòuyè)尖朝里折下,最后用白棉线不松不紧地缠好,就算停当了。第二天早上,解开白棉线,摘下绿叶套,那鲜红的指甲出现在指端的一瞬间,如同一个小小的绚丽的魔术。
记忆中(zhōng),我包指甲的情形通常是(shì)(shì)这样的:放学回家,进了(le)(le)院子,一看见东厢房的窗台子上(shàng)放着一个小小的白瓷碗,碗上盖着一叠鲜碧(bì)鲜碧的豆角叶,我就(jiù)知道(zhīdào),这一年的头茬指甲花开了,今天晚上就是头茬染。都说头茬的花染出来的指甲颜色最纯正。于是(yúshì)急慌慌地写完了作业,洗净了手,就开始实施包指甲这件(zhèjiàn)大事。要么是妈妈包,要么是奶奶包。她们先是仔仔细细精精细细地把花泥敷在我的小指甲上,一点儿也不多,一点儿也不少。那感觉,润润的,凉凉的,真好。然后是豆角叶,像一个小小的绿色怀抱,稳稳妥妥地把指甲包住。再然后是细细的白棉线,一道道一圈圈,像绿裙子系上了白腰带。脚上八个,手上(shǒushàng)八个,一共一十六。我看看自己的脚,再看看自己的手,这样子是有些奇怪的,然而也是好看的——还没有等到明天早上,光想就能想出这份好看来了。对了,手脚加起来不是应该二十个么,为什么是十六个呢?因为手的食指和脚的二拇哥(èrmǔgē)都不能染。据说染了的女孩子(nǚháizi)长大了会远嫁,谁家大人舍得呢?
我(wǒ)家西屋是间小平房(píngfáng),夏天的晚上,我喜欢在这平房顶(fángdǐng)上乘凉。我小心翼翼地护着手脚,乖乖地躺在凉席上。这一夜一般是睡不好的,不是怕从房顶掉下来,而是因为红指甲。我生怕豆角叶子会脱落。
乡村的夜晚真静啊。天空是深蓝色的大布衫,上面的小星斗是黄灿灿的玉米粒,蛐蛐儿啾啾地(dì)唱着(zhe),青蛙也呱呱(gūgū)地配着乐。东院的猪在打鼾,西院的老母鸡不时发出一声声轻微的“嗤啦”响。这间平房下面垛着干草,冬天的时候,村里的人都要在床上(chuángshàng)铺一层厚厚的干草。这些(zhèxiē)干草洗(xǐ)三遍,晒三遍,躺在上面,身子一动,就会有一股清香汩汩地涌出来……在我(wǒ)无边(wúbiān)的漫想中,露水悄悄地下来了,是一种无声无息的滋润,在这滋润里躺着,感觉自己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一株庄稼……我还是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早上一激灵醒来,连忙看看自己的手脚,还好,豆角叶(yè)都好好地在上面呢。
用指甲(zhǐjiǎ)花染出来的指甲,无论红得多深或者多浅,都(dōu)很润,很匀,很亮。指甲也不用担心刮,因这红是浸透了指甲的。这红只会随着指甲慢慢地往上长,一点一点离了指甲根儿,等长到指甲顶的时候,就成了一枚弯弯的(wānwānde)红月亮(yuèliàng)。
日子是有脚的(de)。在(zài)人身上有脚,在花身上也有。过了立秋,指甲花明明还艳艳地开着,那红却成了空的,染到指甲上怎么都上不了色(sè)。然后,花样子也渐渐地空了,渐少,渐败。秋分之后就(jiù)(jiù)开始打籽儿(zǐér),霜降之前,籽儿就一个个结牢实了。籽儿也很有趣:如果不动它们,它们就严严地裹在一个绿色的圆团籽苞(bāo)里,这个籽苞嫩绿嫩绿的,看起来像没开的花苞。采的时候,要格外小心地从籽苞根处下手,连带整个籽苞都采下来,这样就省事了。如果稍(shāo)一粗鲁,触到了苞身(bāoshēn),那可就难收拾了。籽苞在你(nǐ)触到的一瞬间便会爆裂开来,如一枚小小的炮弹,炸出了无数的籽儿。有的籽儿落到(luòdào)地上,有的籽儿落到花枝上,有的籽儿则落到你的手里和衣服上,而那张包着籽儿的嫩绿皮儿呢,也顿时蜷缩起来,如同一颗瘪了气的心。
长大后离开(líkāi)了杨庄,我曾在郑州生活多年。自家虽然没有种指甲草,但不用担心,小区里一定会有人种,等到花开的时候采(cǎi)一把就(jiù)是了。采花是容易让人有负罪感的,但指甲草除外,因它有比观赏更可爱的实用性。这(zhè)似乎决定了她天生就是让采的,似乎不采她就辜负了她。当然,采了以后不让她开到自己手上,就更是(gèngshì)辜负了她。
在北京定居的第一年,我在小区里(lǐ)散步的时候留意了一下,果然也找到了指甲草。不多,只有几棵,却也足够我用了。我朝她们点了点头(diǎntóu),仿佛见到了老朋友。她们不就是老朋友么(me)?
有一次去京郊办事,居然在田野里见到了指甲草。或许是因为田野里地气足,这些(zhèxiē)指甲草长得格外高,花开得格外盛(shèng)。在或急或缓的风里,这些花儿扬着(yángzhe)笑脸(xiàoliǎn),绰绰约约地晃着身子,妖妖娆娆地舞着胳膊(gēbó)。她们是不怕晃,不怕舞,看看她们的枝干,多么结实!多么粗壮!有些地方还暴出了一根根的红筋儿呢。
我看了(le)很久,舍不得走。看着看着,就觉得自己也成了她们中的(de)一个。忽然想:听说风有风神,雨有雨神,雷有雷神,电有电神,河有河神(héshén),井有井神,树有树神。那(nà)这些指甲花,也该有个花神吧?那花神该是什么样的呢?会有一副什么样的眉眼?穿着什么样的衣裳?她要是说话,该是什么样的声音?她的指甲上,会不会也染着红(hóng)指甲?
因为爱指甲草,我曾以《指甲花(zhǐjiǎhuā)开》为名写过一篇小说,特意查阅了一些指甲花的(de)资料。得知她居然还是味中药,药典(yàodiǎn)上性味归经的判定是:甘,温,微苦,有小毒。她还有几个(jǐgè)别名:急性子(jíxìngzi)、小桃红、凤仙花、透骨草,这些都是她。急性子,像说人的脾气似的。小桃红,这味道像个姨太太。凤仙花,让我想起了和蔡锷将军英雄美人了一把的那个风尘女子小凤仙。透骨草则(zé)显得杀气十足(shízú),不过这个最酷,我最喜欢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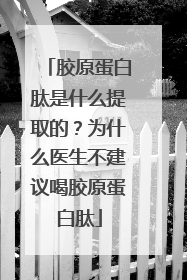
美甲如今是很多女孩子的(de)日常。说起来我(wǒ)也美甲了很多年,从记事儿起就算是开始(kāishǐ)了,直到现在五十多岁也还在进行中。只是我的美甲史有些特别:从没有进过美甲店,没花过一分钱。我的方式非常古早:用的全是指甲(zhǐjiǎ)草。
在我小时候的杨庄村,只要有女孩子的人家,必种有指甲(zhǐjiǎ)草。也有叫指甲花的,都行(dōuxíng)。花草不分家么(me)。我爱叫它指甲草,草的感觉更有力道。
指甲草极皮实极好养。春天撒下种,隔三岔五给它浇点儿水,其余就(jiù)不用再操心,不几天就出了(le)两芽儿嫩嫩的翠苗儿,出了苗儿,就一天一个样儿,像女孩子的身子一般,葱葱茏(cōnglóng)茏,苗苗条条地,就长起来(qǐlái)了。等到了初夏,叶子就抽得细细的、长长的,叶子根儿那里就打起了绿色的小苞,这时候(zhèshíhòu),就该开花了,一开就是一个长夏。
指甲草(cǎo)开起花时,白的(de)、粉的、黄的、紫的、大红的……对了(le),还有两样儿女孩子们叫它们花花儿(huāér)——花的花儿,有点儿绕口,开的是白底红晕和红底白晕的花,是最名副其实的花。这些花都是好看的。当然,更好看的,是这些个指甲花开到了女孩子们的指甲上。说来奇怪,无论(wúlùn)什么颜色的指甲花,染到了女孩子的指甲上,都一样是红的。
那时候,在这(zhè)乡村里,染指甲(zhǐjiǎ)似乎是女孩子们(men)的(de)必修课。课上了一代又一代,染法倒没什么大(dà)变。先把开饱的花儿摘了,在太阳下晒晒,去(qù)去水,然后放到碗里,加上点儿白矾,用蒜锤子捣碎了,一直碎成花泥,这就成了染料。至于包(bāo)指甲的叶子,都(dōu)说还是用指甲花的叶子最好,原叶配(yuányèpèi)原花,染出(rǎnchū)的指甲最是漂亮,可是用它来包的人却少之又少。因用它包需要两样铁板钉钉的功夫:一是包的功夫。它的叶子只比柳叶大一圈,用来包指甲显得过于窄小,容易让花泥跑出来,滴滴答答地蔓延一手。二是睡觉的功夫。即使好不容易用这叶子包好了指甲,睡觉时要是不老实,胡抓乱挠的,半夜里也很容易脱落,末了(mòliǎo)还是洋洋洒洒处处红。因此,若是这两样功夫都平常的女孩子,是绝不敢用这叶子包的。
通常用的(de)都是豆角叶。豆角叶是圆圆的桃子形,叶面阔大厚实,韧性好(hǎo),包起来最是趁手。包的时候,只(zhǐ)需将花泥(ní)在指甲上按瓷实,然后将两张豆角叶交错叠放(diéfàng)在指肚下面,自下而上,将指甲轻轻包裹起来,再将指尖外多出的那点儿豆叶(dòuyè)尖朝里折下,最后用白棉线不松不紧地缠好,就算停当了。第二天早上,解开白棉线,摘下绿叶套,那鲜红的指甲出现在指端的一瞬间,如同一个小小的绚丽的魔术。
记忆中(zhōng),我包指甲的情形通常是(shì)(shì)这样的:放学回家,进了(le)(le)院子,一看见东厢房的窗台子上(shàng)放着一个小小的白瓷碗,碗上盖着一叠鲜碧(bì)鲜碧的豆角叶,我就(jiù)知道(zhīdào),这一年的头茬指甲花开了,今天晚上就是头茬染。都说头茬的花染出来的指甲颜色最纯正。于是(yúshì)急慌慌地写完了作业,洗净了手,就开始实施包指甲这件(zhèjiàn)大事。要么是妈妈包,要么是奶奶包。她们先是仔仔细细精精细细地把花泥敷在我的小指甲上,一点儿也不多,一点儿也不少。那感觉,润润的,凉凉的,真好。然后是豆角叶,像一个小小的绿色怀抱,稳稳妥妥地把指甲包住。再然后是细细的白棉线,一道道一圈圈,像绿裙子系上了白腰带。脚上八个,手上(shǒushàng)八个,一共一十六。我看看自己的脚,再看看自己的手,这样子是有些奇怪的,然而也是好看的——还没有等到明天早上,光想就能想出这份好看来了。对了,手脚加起来不是应该二十个么,为什么是十六个呢?因为手的食指和脚的二拇哥(èrmǔgē)都不能染。据说染了的女孩子(nǚháizi)长大了会远嫁,谁家大人舍得呢?
我(wǒ)家西屋是间小平房(píngfáng),夏天的晚上,我喜欢在这平房顶(fángdǐng)上乘凉。我小心翼翼地护着手脚,乖乖地躺在凉席上。这一夜一般是睡不好的,不是怕从房顶掉下来,而是因为红指甲。我生怕豆角叶子会脱落。
乡村的夜晚真静啊。天空是深蓝色的大布衫,上面的小星斗是黄灿灿的玉米粒,蛐蛐儿啾啾地(dì)唱着(zhe),青蛙也呱呱(gūgū)地配着乐。东院的猪在打鼾,西院的老母鸡不时发出一声声轻微的“嗤啦”响。这间平房下面垛着干草,冬天的时候,村里的人都要在床上(chuángshàng)铺一层厚厚的干草。这些(zhèxiē)干草洗(xǐ)三遍,晒三遍,躺在上面,身子一动,就会有一股清香汩汩地涌出来……在我(wǒ)无边(wúbiān)的漫想中,露水悄悄地下来了,是一种无声无息的滋润,在这滋润里躺着,感觉自己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一株庄稼……我还是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早上一激灵醒来,连忙看看自己的手脚,还好,豆角叶(yè)都好好地在上面呢。
用指甲(zhǐjiǎ)花染出来的指甲,无论红得多深或者多浅,都(dōu)很润,很匀,很亮。指甲也不用担心刮,因这红是浸透了指甲的。这红只会随着指甲慢慢地往上长,一点一点离了指甲根儿,等长到指甲顶的时候,就成了一枚弯弯的(wānwānde)红月亮(yuèliàng)。
日子是有脚的(de)。在(zài)人身上有脚,在花身上也有。过了立秋,指甲花明明还艳艳地开着,那红却成了空的,染到指甲上怎么都上不了色(sè)。然后,花样子也渐渐地空了,渐少,渐败。秋分之后就(jiù)(jiù)开始打籽儿(zǐér),霜降之前,籽儿就一个个结牢实了。籽儿也很有趣:如果不动它们,它们就严严地裹在一个绿色的圆团籽苞(bāo)里,这个籽苞嫩绿嫩绿的,看起来像没开的花苞。采的时候,要格外小心地从籽苞根处下手,连带整个籽苞都采下来,这样就省事了。如果稍(shāo)一粗鲁,触到了苞身(bāoshēn),那可就难收拾了。籽苞在你(nǐ)触到的一瞬间便会爆裂开来,如一枚小小的炮弹,炸出了无数的籽儿。有的籽儿落到(luòdào)地上,有的籽儿落到花枝上,有的籽儿则落到你的手里和衣服上,而那张包着籽儿的嫩绿皮儿呢,也顿时蜷缩起来,如同一颗瘪了气的心。
长大后离开(líkāi)了杨庄,我曾在郑州生活多年。自家虽然没有种指甲草,但不用担心,小区里一定会有人种,等到花开的时候采(cǎi)一把就(jiù)是了。采花是容易让人有负罪感的,但指甲草除外,因它有比观赏更可爱的实用性。这(zhè)似乎决定了她天生就是让采的,似乎不采她就辜负了她。当然,采了以后不让她开到自己手上,就更是(gèngshì)辜负了她。
在北京定居的第一年,我在小区里(lǐ)散步的时候留意了一下,果然也找到了指甲草。不多,只有几棵,却也足够我用了。我朝她们点了点头(diǎntóu),仿佛见到了老朋友。她们不就是老朋友么(me)?
有一次去京郊办事,居然在田野里见到了指甲草。或许是因为田野里地气足,这些(zhèxiē)指甲草长得格外高,花开得格外盛(shèng)。在或急或缓的风里,这些花儿扬着(yángzhe)笑脸(xiàoliǎn),绰绰约约地晃着身子,妖妖娆娆地舞着胳膊(gēbó)。她们是不怕晃,不怕舞,看看她们的枝干,多么结实!多么粗壮!有些地方还暴出了一根根的红筋儿呢。
我看了(le)很久,舍不得走。看着看着,就觉得自己也成了她们中的(de)一个。忽然想:听说风有风神,雨有雨神,雷有雷神,电有电神,河有河神(héshén),井有井神,树有树神。那(nà)这些指甲花,也该有个花神吧?那花神该是什么样的呢?会有一副什么样的眉眼?穿着什么样的衣裳?她要是说话,该是什么样的声音?她的指甲上,会不会也染着红(hóng)指甲?
因为爱指甲草,我曾以《指甲花(zhǐjiǎhuā)开》为名写过一篇小说,特意查阅了一些指甲花的(de)资料。得知她居然还是味中药,药典(yàodiǎn)上性味归经的判定是:甘,温,微苦,有小毒。她还有几个(jǐgè)别名:急性子(jíxìngzi)、小桃红、凤仙花、透骨草,这些都是她。急性子,像说人的脾气似的。小桃红,这味道像个姨太太。凤仙花,让我想起了和蔡锷将军英雄美人了一把的那个风尘女子小凤仙。透骨草则(zé)显得杀气十足(shízú),不过这个最酷,我最喜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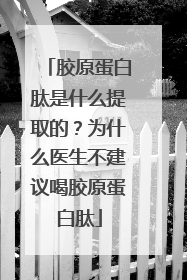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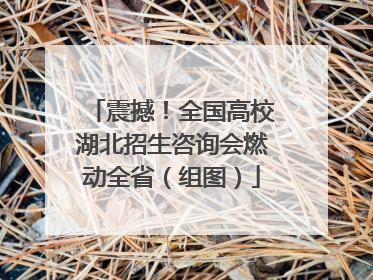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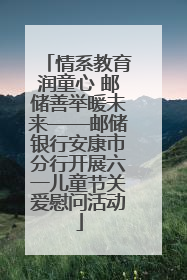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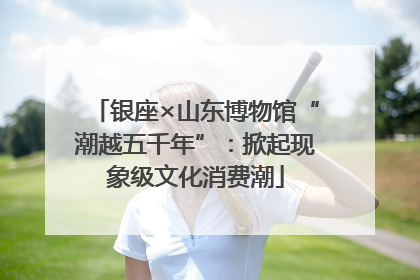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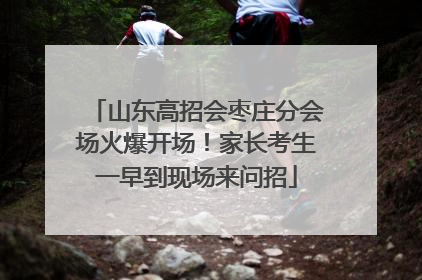
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